【當代散文】林央敏/故鄉墳城衰微記
1978年初冬,第一號高速公路全線通車後,每次回到故鄉,我總會站在村前的恩主公廟口——小時候常逗留的地方——張望嘉義交流道上方的車流,一彈指,想像活躍起來,「騅駓駰駱驪騮騵,白魚赤兔騂騜鶾」,彷彿看到蘇東坡的〈牧馬圖〉在動、在變形,變成一幕電影,各色品樣的大小馬匹在天路上奔馳,南來北往都是騏與驥,病驢瘦駑不得上大路。
翌年初夏,走高速公路的公路局(台汽客運)和幾家野雞車開通台北—嘉義線後,我好奇嘗鮮,不坐鐵路火車,改乘馬路巴士返鄉,進入縣境,血液開始悸動,近鄉情更怯,又是我首次可以從高處瀏覽家鄉風景,過了牛稠溪橋後,被文明栽植了幾座洋房的老家村落便收入雙眼,雙眼彷彿錄影機那般逐一拍取小時候的記憶,似乎連故鄉的溫情也被捕捉到軟片裡,在我的眼瞼中栩栩然沸騰起來。剎那間,住著吾村先人的那片墓仔埔衝進鏡頭,墓碑似門,陰宅亦宅,覺得這座處在村野的亂墳小聚落已擴大範圍,顯示「人口成長」,心裡直覺它就像一座「墳墓之城」,小時候到此放牛、割草、掃墓,即使在墓園中踏破數雙草鞋布鞋也不曾產生這種感覺,卻在當日高速的嘶嘶聲裡看到它成為迷人的墳城。
回家後,放下行李便騎車出村,直奔東郊墳城。自從四十年前,跟隨父執輩來為早逝的曾祖父撿骨,將骨金裝罎重新安葬在城外的竹林僻地後,就很少再走進這座墳城,直到有一回因為感念二叔公生前對我的關照恩情,才邀同小堂叔前來探望叔公的墳塚並奉上一番喃喃祭禱,這也大約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此後記憶中雖然不復入城來,但仍然會敲擊我的心念。馬奎斯這樣說的吧:故鄉就是埋葬祖先的地方。所以這裡也是一種故鄉,它和吾鄉村人連通著的血緣,可以溯流迴之到遙遠!
我到達時,太陽已經偏西,燦爛的霞影餘暉披在那排墳城邊緣的竹林上,有一些光芒好像被竹葉篩過,形成管狀的光柱斜射在近處的林投樹上。林投樹叢就像是這座墳城的西城門,小時候每逢三日節或清明掃墓,以及偶爾與童年玩伴來這裡採割林投的帶刺脩葉,大多是從這個角落進出,城門前曾矗立著一根石柱指明這是本鄉的第十八公墓,如今這支「路觀牌誌」已傾倒,城門左側原本「埋居」吾村首富之葉家大媽的那座碩大堡壘已消失,想必她的後嗣也為她「抾金」了,原地只剩一片蕀苓占據的小草原。
墳城北郊原有一條滿身生鏽的台糖鐵道,小時候每逢砍收甘蔗時節,來這裡割牧草或遊玩的小朋友,包括我,都會在這個路段和使力拉著滿載甘蔗的拖板火車同行,看年邁的蒸氣火車母氣喘如牛的爬著小斜坡,並且放慢速度彷彿拖不動時,趁機在最後一節偷抽幾根甘蔗,直到會社的隨車人員發現時吹起急急如律令的哨子才罷手。大約我進城讀書的青年時期,不知為何村人不再栽植甘蔗,於是這條專運甘蔗的五分鐵道便壽終正寢,變成死蛇般躺在那兒,想像裡只能載著往來的鬼客神差吧?而現在,不知哪一年,連鐵軌也被移除了,只留存在我的心裡和夢裡,因為夢裡,我曾經有一次不知為什麼會在日薄西山時,必須孤單一個小孩從溪底沿著鐵道回家,踽踽涼涼的走到墳城這一段時,忽然出現兩隻惡鬼跑來要抓我,我一驚嚇,開始落荒狂奔,可是不知為什麼明明用力奔跑卻覺得土地有吸力般,腳步變得很沉重,正要被惡鬼抓到時才驚醒過來。
想到這裡,我穿過草原,跨步走入墳城,幾株朽木橫徑,一朵一朵的紅色大靈芝裡豁然湧出一群一群的螞蟻雄兵攻過來,我縱躍幾步,迅速閃過。原來墳城還有這般凶猛的陸軍在守護。放眼看去,看出斯城也,依三尺之山,傍五寸之水,風光若江南,但此地不是江南,而是流經故鄉這段牛稠溪的南畔。早年,當我逸興通幽遄飛時,會把每座墳塚看做每戶鬼家,想像《幽明錄》與《列異傳》分處西、南兩區,《冥祥記》在北埠,《靈鬼志》在東津,蒲松齡的《聊齋》就在水街十三號,那麼即使有古代遊魂飄泊到此地,也應有一席棲地讓祂寄鬼籬下,前方埠頭之巔的一間簡陋小屋,就是收容無家可歸的大眾陰廟,少年時,小堂叔有一次帶我到這片墓仔埔採食一種叫「刺波」的野草莓就曾經走到那間陰廟,也在小堂叔的膽量加持下,我小心翼翼地把眼睛湊近壁上的小洞,窺見裡頭原來儲藏著成堆的骷髏,此後將近一甲子不曾再走近,今天我也不想再深入市區,因為西斜的太陽已轉弱,沒有足夠的陽光可供四處遛躂了。
我只就近看看被草堆蒙住的土墩和土墩前的墓碑,墓碑如門,刻著「渤海」、「龍巖」、「延陵」、「天水」、「潁川」、「江夏」……以此表明死者生前的堂號身世或淵源,由此看來,吾村不但沒有省籍歧視,還曾經住著齊桓公的子民之孫、吳季札的同鄉、諸葛亮的鄉親和愛洗耳朵的夷齊族裔……不知他們的後人是否還定居吾村,也許已有不少村人舉家棄農北漂了,因為在過去三、四十年間,自從政府開始把台灣北部的農地一甲又一甲劃作工業區,並設定嘉南平原的沃野千里還須繼續種稻米,這裡便開始人口外流,流向更能生長金錢的北地。於是早年被譽為台灣精華區的平原反而成了鄉窮壤僻的草地,連帶的這座墳城也衰微了。
記得四十年前,我恍然一瞥,忽見這片公墓也如人間桑梓的起落變遷,由村落「發展」為城鎮而叫它「墳墓市」時,特意不為掃墓祭祖,只為觀光遊覽而入城,那時我看市中心,每戶陰宅都面曠背山,在有限的土地上也要體現堪輿家和地理師的學問,結果顯得擁擠不堪,最後雜亂無章的擴大範圍,亂墳離落的郊區伸展到原先的番薯田。於是我突發異想,覺得墓仔埔也應有都市計畫,認為活人應為死人想,除了替他們築一戶舒適的家,讓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外,還要把墳城規畫成公園。相對的在人口爆炸的台灣,人還生,鬼不死,鬼簿恐已滿,所以死人也應為活人想,不與生人爭土地。數年後希望有高樓在這裡長出,每座高樓住著一家鬼族的屍骨,甚至所有作古的村人都可以同處一幢大廈社區。如今看來,這個異想中的高樓大廈彷彿以另一種形式實現,幾年前開始矗立在西村南郊的公立納骨塔就是墳城往天空長高的應驗,我猜想舊墳之主被子孫撿骨後,應是被重新安家到納骨塔,加上火葬之風吹偃土葬之俗,使得墳城墓厝漸稀疏,這樣,墳城衰微反而是好事。
最後,我的思緒竟然遊走到自己生命的終點時,自問當我歸去來兮那一天,我應如何處置這身行將腐臭的皮囊呢?想著:讓烈火煉化成灰燼是必然,但這一公斤重的灰燼還需占據半坪土地或三分之一立方米的塔位嗎?既然古詩云:「古墓犁為田,松柏催為薪」,亞歷山大的屍泥都會成為野花的肥料,凱撒的朽塵曾被土水匠糊入一片牆。那麼教風吹向天,教河帶向海,無論何處都能塵歸塵,便是我的老有所終,管他靈魂飄飄何所之?也就用不著念經超渡!
思緒如潮躍過彼岸,看到自己人生的結論後,也看到被彩霞紋身的雲開始由紅轉黑,夕陽已落入地平線,我不能再踟躕,便踩著微弱的光快步走出墳城。
加入 琅琅悅讀 Google News 按下追蹤,精選好文不漏接!逛書店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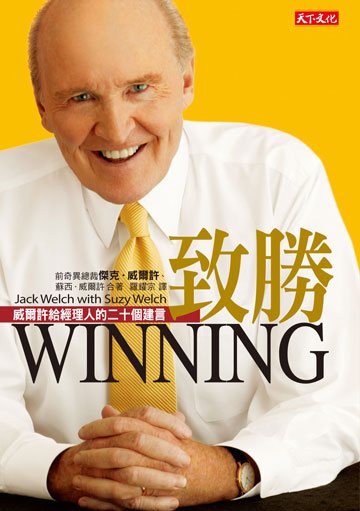





FB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