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第16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 散文組 三獎:林子喬〈尋光〉

本篇「光」從極光變成一盞檯燈,讀來頗有共鳴,而對於女性情感描寫得極為細緻,光的意象有多重寓意。 ──方梓
本文從女兒視角觀看母親,充滿同情與理解,文中絕美的極光轉為黯淡平凡的燈泡光,象徵母親不同的人生階段,家庭生活消磨了母親的銳氣,使她逐漸委頓。文字帶有淡淡的惋惜與憂傷。 ──簡媜
窗戶透出的光是來自對面一戶晚歸的夫婦餐桌上,微微刺眼的光線在一陣碗盤的碰撞過後也跟著歇下了,身旁瞬間只剩妹妹熟睡的呼聲,還有從窗戶靜靜滲入的,遠方大馬路上汽車呼嘯而過的聲響,現在已經是深夜。房間裡的燈早已經關了,只能藉著天花板上映出的昏黃在黑暗中辨出一床粉色,那是客廳燈光的顏色,是一點橘黃的光在漆黑裡暈開。母親還沒睡。
有記憶以來,母親便一直是個張揚的女子,明豔而且固執。小時候的我總喜歡從她一櫃子的裙裝裡選出一件我覺得尤其適合她的,軟磨硬泡的要她穿上;喜歡在她化妝的時候賴在她身邊,央求她在面紙上印一個唇印給我;喜歡在她下班回來後抱著她,聞她身上保養品香香的味道。那時的她還在工作,也總是晚歸,就連假日加班的情況也不在少數,在我大多數關於白天的記憶裡,陪伴我和妹妹的也幾乎都是父親。有時候我會跟著母親到公司去,但更多的時候我待在房間裡等她,在沙發上等她,在浴室門邊等她,等她聽我講今天老師跟我說的故事,聽我說誰又綁了哪個可愛的髮型,最後兩個人一起累到睡著。關於這些的記憶現在大抵只剩一室漆黑裡難掩興奮的尾音、浴室門縫底下的一束光亮,還有在滿滿的疲倦之後,依然放著光的她的眼睛。母親的心是夜晚的一條街,街上平整的柏油路面幾乎混在了黑夜裡,只有一盞路燈漾著暖暖的昏黃的光,而她穿著裙裝、長髮飛揚,撐起夜色向我走來。
我再大一點後,母親開始跟我和妹妹說起她以前的故事,那是她還住在外婆家的時候。她說她登過玉山,看過恆河河畔的喪禮,也曾經被大象用鼻子捲住腰部然後高高舉起。說起這些的時候母親似乎就不再只是母親,她的臉上多了一些我從沒見過的色彩,極光一般的絕美陌生,我似乎在那道光裡看到了外婆家那條蜿蜒崎嶇的山路,遍地的小碎石子為路面鋪出了稜角,年輕時的母親在夜幕下一身輕盈,踏著月色向前行去,她把滿天星子裝在了眼睛裡。
更之後的日子,母親提起那些的次數也少了,或許是能說的都說完了吧,那個令我感到陌生的她似乎早已成了灰色的記憶。母親也不再晚歸,因為她已經辭去工作,成了專職的家庭主婦。父親說母親已經在無數次的飛行裡把自己弄得遍體鱗傷,現在的她可以儘管回到屋裡暖黃的燈光下,再不用理會窗外的風雨飄搖。而我也真的沒再見過她拖著一身疲憊回家的樣子。自此之後母親的生活變得簡單,需要惦記的從下屬的工作進度,換成了冰箱裡的高麗菜紅蘿蔔;需要過目的也從密密麻麻的財務報表,換成了滿是鉛筆痕跡的作業簿;皮包裡最常拿出來的不再是辦公大樓的門禁卡,而是出示就能享有優惠的生鮮超市會員證;記事本上最頻繁出現的也不再是開會與簡報的日程,而是代表著不需要為父親準備便當的小記號。那時的我很快的習慣了母親終日待在家裡的日子,也很快的把之前求而不得的菜肴視為理所當然,我以為我再也不需要等她。
但我不知道那天我到底等了多久,大概比之前的每個晚上都要久上許多,可門始終沒有打開。我依稀記得樓梯扶手的影子在家門口的地上拉得斜長,牆壁粉刷的白色斑駁出了水泥灰,課本裡的烏龜已經跑贏了兔子無數次,終於父親和妹妹的腳步在樓梯間踩出回音,落日的橘色光芒打在我臉上。
「我在海邊看螃蟹。」電話那端,母親的聲音幾乎要揉碎在風聲潮聲裡,聽起來好遠好遠。我似乎又看見了那道極光。
也許母親正蹲在北海岸的沙灘上,看著一隻正張牙舞爪的,翻不過身的螃蟹。她應該一身輕便,隨身的除了平時愛用的深紅色斜背包再沒有任何東西,就連緊跟著的一串腳步也幾乎都被海浪帶走了,只剩下零零散散幾個深淺不一的印子。離岸邊更遠的海上開過的郵輪大多是我看也沒看過的,幾艘勉強還認得出來的好像是好久以前少數幾個母親不需要加班的周末,她帶著我和妹妹到基隆港邊一艘艘指給我們看的。風似乎愈來愈大,夾雜著岸邊特有的鹹腥氣味往天與海的交界吹送,強勁得彷彿能讓母親乘風飛起,有一瞬間我以為她已經站在了甲板上。可她最後還是接起了電話,另一頭的我扁著嘴巴喊她母親。於是她又回到了沙灘上,我似乎能想像她終於鬆開了一直緊緊握著的雙手,右手掌心被硬物壓出了紅痕,一顆白色的貝殼靜靜落在一旁。沙灘上的螃蟹似乎累了,招搖的螯隨著夕陽落下,沒再舉起來過。
母親回來了,在天色全暗之前。那天的她站在巷子口,平靜得彷彿只是出門倒了一趟垃圾回來,路燈昏黃的光壓在她身上,扎眼得幾乎看不清輪廓,是那個我熟悉的母親。自此之後我再沒看過極光,那也是我最後一次等她。母親大概是從這之後開始習慣市場和家裡兩點一線;開始習慣一言不發的十多個小時;開始習慣一個人在沙發上靜靜坐到凌晨。她擁有一雙能夠讓她飛得又高又遠的翅膀,只是她把翅膀收在了屋簷下。這時的母親已經離外婆家的那條山路很遠了,那條沒有燈的山路,她仰頭能看見的也不再是一片星斗璀璨,而是一盞抬手可及的家門前的微黃色亮光。
後來母親會和我們說起的已經不是之前那些遙遠的地名,更多的是關於回到屋簷下之後的自己,她的聲音並沒有隨著時間流逝變得蒼老,與之前不同的只有尾音,被雲淡風輕後的疲憊拖著止不住下沉。我們兩人單獨講話的時間依舊是深夜,但地點已經不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房間,我也不再擔心她會在聽我講完前就撐不住睡著,因為客廳的燈總是會在我睡著後又靜靜的獨自亮了許久,可母親的眼裡卻沒有了那時一片漆黑裡也能看見的光彩。我想她大概是把那道光芒給了客廳的吊燈吧,那盞泛著柔和光線的燈火。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習慣讓臥室天花板上映出的橘黃成為一天的最後一抹顏色,但我不再看著她的眼睛。
就這樣過了一兩個年頭,我早已不是那個會纏著她要唇印的女孩,而母親也有好長好長的時間不曾再穿上裙裝,化妝桌上的瓶瓶罐罐在不知不覺間慢慢少了,最後只剩下一罐全身都能用的乳液。六百多天的日子並沒有讓陽台上的植物多長高幾公分,但已經足夠讓母親記得我和妹妹班上大多數同學的名字,也足夠讓我忘記她眼裡曾經的那抹光亮。母親的廚藝比起從前已經熟稔了許多,她也漸漸能夠串聯起我曾經和她說過的每一件事情,但母親依舊晚睡,在滿室昏黃色光包圍間,她似乎一直望著窗外,就如同小時候的我總是望著她的眼睛。母親渴望飛翔,想要張開雙翼擁抱風雨後的彩虹,可父親和她不一樣,他看著的不是窗外,而是母親那雙再禁不住折騰的翅膀。
又過了一段時日,我待在家裡的時間愈來愈少,每天晚上聽我滔滔不絕的也漸漸不再是她,我甚至想不起我們上一次夜間談話是什麼時候。但我永遠忘不了那個夜晚,離家兩個禮拜的我剛剛歸來,儘管拖著一身疲憊卻還是和她從白天說到了深夜,睡著之前母親告訴我她在我的眼中看到了星火,我突然明白了,她眼裡的光終究不是給了吊燈。
我知道我終將走上母親的那條山路,但我看不清山路盡頭的那抹亮光究竟是什麼,或許也會是一盞昏黃的燈吧,靜靜泛著的光芒溫暖得讓人忍不住靠近。我曾經很羨慕母親擁有一盞能夠支撐著她的燈火,在她累得無法飛翔時接住她往返;我曾經以為母親會在溫暖的光下慢慢好起來,但最終那雙翅膀被困在了燈光裡,任憑她怎麼掙扎也張不開。後來母親不再試著揚起雙翼,可她似乎又比剛辭去工作時還要脆弱了許多。我多希望那盞燈從來沒有出現,我多希望母親能夠找回那道屬於她的極光,但在那道極光掠過腦海的瞬間,我開始害怕見到那雙盛滿星光的陌生眼眸。
橘黃色的燈依舊亮著,閉上眼之前,我依稀看到了幼時尋不著母親的我,蹲在路旁緊咬著牙卻還是哭出了淚來。
●決審記錄刊於聯副部落格:http://blog.udn.com/lianfuplay
聯合報 D03 聯合副刊 林子喬(明道中學二年級) 2019/09/29

逛書店
猜你喜歡
贊助廣告
商品推薦
udn討論區
- 張貼文章或下標籤,不得有違法或侵害他人權益之言論,違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 對於明知不實或過度情緒謾罵之言論,經網友檢舉或本網站發現,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 對於無意義、與本文無關、明知不實、謾罵之標籤,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標籤、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下標籤。
- 凡「暱稱」涉及謾罵、髒話穢言、侵害他人權利,聯合新聞網有權逕予刪除發言文章、停權或解除會員資格。不同意上述規範者,請勿張貼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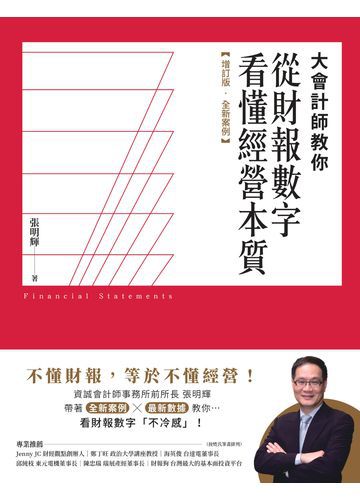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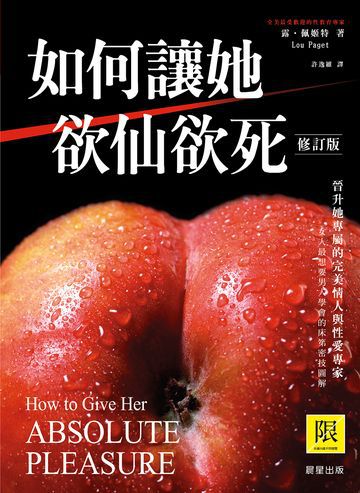




FB留言